我眼中的 Julian Assange

前言
維基解密(Wikileaks),長久以來在我腦中都是一個像都市傳說一樣的存在,好像知道有那麼回事,卻也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
阿桑奇(Julian Assange)維基解密最有名的創辦人,會真正進入我的視野,也是很最近的事:大概是於 2021 年一月的一則新聞。當時阿桑奇已經在英國被「軟禁」在監獄幾年了,英國法院駁回了美國的引渡要求,因為判斷 Assange 有自殺的風險。那時候讀了幾篇新聞報導,才發現原來維基解密跟史諾登不是同一件事,上網看了些新聞,對於這個案子還是滿懷希望的。隨後在 2022 年初,crypto 圈颳起一波金援阿桑奇的風潮,用 DAO 的形式讓任何人都可以贊助阿桑奇的法律團隊,當時比較認真地看了案件的細節(總是捐錢前比較認真),才對整個事件有比較全面的理解。
轉眼間,又兩三年多過去了,期間經歷了美國政府的上訴、再次被裁定引渡、 再次上訴、被拒絕審理、再次上訴幾番折騰,上週二已經是阿桑奇最後一次在英國,法律上可行的引渡聽證會,英國政府可能會在三月中旬以前做出裁決,如果上訴被駁回,阿桑奇最快可能在一個多月內就被引渡到美國接受審判。
這幾天又認真的整理了一些資料、讀了更多的報導、也開始看阿桑奇與幾個人聯合出版的對話紀錄:cypherpunk: Freedom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慢慢在自己的腦袋裡形塑出一個更加立體的人物,也些微改變了一下我看整個事件的立場。
以下這篇文章記錄的是我的思路過程,前半段主要在介紹這個危機解密事件的來龍去脈,後半段則是更多關於阿桑奇這個人的介紹,還有我覺得現階段能下得最好結論。
前情提要:維基解密與電報門事件

維基解密(WikiLeaks),直白點講就是一個爆料網站,它讓任何人可以在上面向編輯團隊分享機密文件,不用擔心自己的身份被揭露,接著再由這些編輯審核過後,以維基解密為平台發表這些匿名爆料。在 Cypherpunk 一書中,阿桑奇這樣形容維基解密的核心理念:
It’s WikiLeaks’ mission to receive information from whistleblowers, release it to the public, and then defend against the inevitable legal and political attacks
也就是說,它是保護「吹哨者」的一個屏障,以揭發社會中的不正義為宗旨。
在 2010 年之前,維基解密不旦被大家視為新時代的正義媒體來源,更是備受推崇,經濟學人還為它頒過「新媒體」獎。
一切直到 2010 年,這一切因為幾個重磅爆料,讓一切變了調:先是在二月,公開了最有名的Collateral Murder
:美軍在伊拉克用直升機機砲掃射路透社記者,附帶攻擊隨後來救助傷患的一輛麵包車,在場人員除了車上小孩無人生還。這項行動稍早由美國軍方聲稱是遭到火力攻擊下的自我防衛,想當然爾,這讓美國政府顏面掃地。那個洩密給維基解密的軍人也有被判刑,不過在 2017 年被歐巴馬特赦。接著是 2010 年末時,同時與美法英德西五家大報社同步的密電門事件(Cable Gate),公開了一批美國各國大使館與美國國務院的電報,其中有揭露腐敗交易的,也有討論外交局勢的,還有反情報部門的各種情報與討論。這次的大爆料比較有爭議性,因為它並不是單單的暴露某一「惡行」,而是更像一次毫無修飾的無差別攻擊(並沒有適度的隱藏被爆料者訊息)。
一系列的爆料,可以在維基解密的維基百科上看到很詳細的介紹,我也是抄來的,就不用說更多了。不過我覺得看完這個清單會發現,這上面的爆料內容是非常廣泛的,當然一直看到美國的影子,但也有英國、冰島、秘魯等等,角色也涵蓋大公司、銀行、政府,呈現一個誰都不怕的架勢。當然了,這麼有底氣是因為這些「解密網站」都是以媒體的角度自居,而這些媒體只要有證據,基本上是很安全的。至少到 2010 年以前都是這樣的。
洩密者與媒體的角色
理論上,洩密這種事情,機構內部的洩密人肯定會違法,就像每個雇主跟僱員之間可能有保密協議一樣,如果違反,肯定有法律責任。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如果有軍人洩漏國家機密,那會被判刑是正常的,無論國家機密是多麽黑暗邪惡,洩漏出去是多麽正義,這樣的行為就是違反了軍人跟國家之間簽訂的契約。
但是媒體的角色就不一樣了,在任何民主國家,媒體都被公認是能監督政府存在的「第四權」。媒體自由是言論自言的延伸,現今,任何民主憲政國家,其言論自由均立憲予以保障,美國憲法增修條款第一條(First Amendment)即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之法律。眾所週知,言論自由不代表大家可以亂說話或誹謗,但是如果有理有據、則發言者是受到最高層級的憲法保障的。
美國歷史上也已經有著名的判例:1970 年代,Daniel Ellsberg 洩露美國軍方機密的五角大廈事件 (Pantegon Papers),被以間諜法起訴,但最終以政府敗訴告終。而更不要說他是五角大廈軍方洩密者的身份。
這點美國政府也知道,因此他們並沒有因為「發布機密文件」起訴阿桑奇,而是先用駭客(commit computer intrusion)這樣的罪名予以起訴,隨後才接著加上了 17 項與「間諜法」(the Espionage Act)相關的指控:主要就是串謀獲取和披露國防資訊。
儘管「起訴他」的法條不是因為他發布機密文件,但大家看得出來,這只是找個罪名先安插上去罷了。在整個起訴過程中,美國是動員全國的力量,並被有許許多多後來被爆出的程序不正義(例如間諜罪起訴的關鍵證人Sigurdur Thordarson 已經公開收回一些對阿桑奇的指證,並聲稱是在 FBI 的強迫下才做證)。這是因為阿桑奇並不是美國人,也沒有生活在美國,因此這個看似令人難熬的十幾年,其實都還指示整個司法遊戲的第一步,先把阿桑奇本人引渡到美國而已。
從 2010 年到現在,阿桑奇基本都處於一個逃亡的狀態,比較有名的就是之前在英國的厄瓜多大使館躲了七年,但之後被轟了出來,從 2019 年至今都以「待引渡」的身份,關押在監獄中。
引渡聽證會
上週剛發生的,就是英國高等法院最後一次舉行的「引渡聽證會」,將會決定是否讓阿桑奇上訴美國的引渡要求。如果上訴被駁回,阿桑奇的律師們也會向歐洲人權法庭提出上訴,但沒有辦法確保會在引渡生效以前被受理。
這也是本案的第二大爭議:一個不在美國生活的非美國「媒體人」,要如何確保自己的新聞自由呢?不難想像,美國政府也不斷地否認阿桑奇媒體人的身份,而是不斷的用「間諜」或是「駭客」來形容他。
大部分支持阿桑奇一派的主要論點也圍繞在「媒體自由」這點。如果今天英國同意了引渡程序,使得阿桑奇被引渡、甚至判刑,那麼不只美國,全世界的記者都要瑟瑟發抖:因為一但你寫的新聞可能被美國政府判定為「披露國防資訊」,你就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國受審。這讓全世界的新聞自由都倒退了,許多人是這樣解讀的,同時也是非常強而有力的論點。

我一開始接觸到的大部分的論點,也都是以這樣的脈絡來敘述整件事情:媒體有自由,沒有人應該因為揭露惡行而被處罰。
當「國家機密」碰上「言論自由」
從上述的脈絡來看,這個「間諜法」看上去是一個荒唐、過時(超過百年前的一戰時制定的)、完全不合理的指控,應該大家也會理應覺得阿桑奇應該於情於理,都站在法理和道德的制高點,而且勝券在握,實在很難想像為什麼這件事還能爭辯個十幾年。
我本來也是這樣想的,直到看到一個簡單的思想實驗,重新思考一下「間諜法」的本質:
假如今天正義的美國跟俄羅斯打仗,美國的「國家機密」就是接下來要攻打的地點,但是現在這個攻打的地點被一個「媒體人」以政府應該公開透明為原則洩漏出來,還刊登在報紙上,造成美國人打輸了,俄羅斯統治世界,燒殺擄掠殺人無數。那這個人的「言論自由」還合理嗎?還是應該要有法律來嚇阻這樣的行為呢?
我想,這應該是美國政府在阿桑奇「電報門」事件後的思考脈絡。當時他爆料的東西確實都是一些骯髒齷齪的事,所以人民很輕而易舉地認為他就是正義的一方。但仔細想想,機密裡面除了有「不可告人的骯髒事」,也一定有有「不可告人的正經事」,那麼究竟該由誰來決定,什麼「該爆料」,什麼「不該爆料」呢?如果這個權力被掌握在媒體手中,是否又太大了呢?
維基解密不只一次的用這樣握在手裡的資料,威脅各國政府:若是阿桑奇有個三長兩短,已經有好幾份被釋出並被大家廣為流傳的「加密後」檔案,只要維基解密說出密碼,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自己拿出備份來解密,妥妥的炸彈。我們一般人很難猜測,這樣恐怖的「機密」,到底只是公佈更多政府不正義的惡行,還是真的讓美國這個國家遭受危機,與維基解密魚死網破的「攻擊」。
如果是戰爭期間,應該許多人會同意政府能有「正義的秘密」,亂公開訊息導致其他人受到傷害的人,應該要被處罰,我想這也是間諜法在戰時被制定的原因。而現在身在資訊戰時代,甚至有人會說:現在的資訊戰是隨時都在打仗,那一樣的「戰時精神」是否還適用呢?
用這個角度想想,又好像沒那麼樂觀了。應該說,好像可以想像一些人會同意用「愛國精神」還有「大政府」的觀點,來覆蓋所謂的基本人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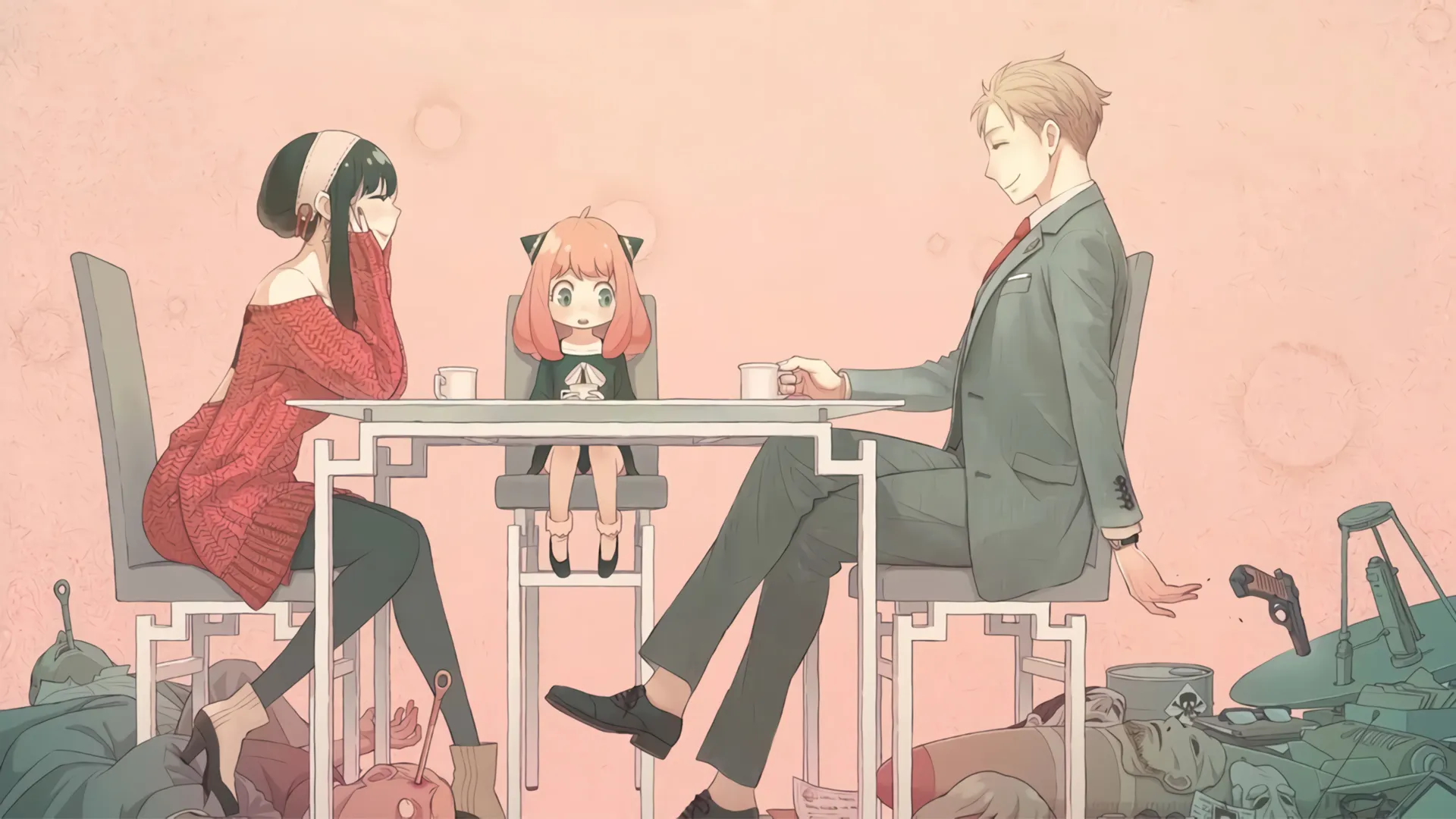
雖然阿桑奇不是間諜,但講到間諜就很想放 Spy Family 的圖片
案件的現況與 我的想法
其實現在整件事雖然常被雙方描述得很「直覺」,但其實有兩大戰場
- 英國是否該引渡阿桑奇
- 阿桑奇的行為是否違返美國法律 儘管他們之間關係緊密,我也覺得值得分開思考
引渡
第一個議題攸關英國,以及所有除美國之外的「友國」,是否要有這樣的引渡先例。所謂「引渡」一直都是每個國家司法機構之間的合作,沒有國際法的規範,本身就隱含了高度的政治化意義。基本上引渡都會要「要求的一方」有明確的證據、符合比例原則、並能證明被引渡者被引渡到該國後,能夠受到更公正的審判。
為什麼這次的引渡造成這麼大的爭議,除了本身美國政府的起訴理由缺乏,普羅大眾也都認為把阿桑奇引渡回美國並不是一個更「公平」的選擇:很明顯美國政府已經動用大量資源來對他提起訴訟,甚至有之前不惜代價發動的暗殺行動,把維基解密形容為「恐怖組織」,一個要往死裡打的架勢。
如果今天案件單純一點:阿桑奇單純在美國被逮捕受審,並不會有這一層的含義。然而正是因為他的身份以及現在人處的位置,迫使歐洲許多團體都加入戰局。因為若真的用這樣的起訴就引渡成功,將會是史無前例的「非美國公民」因為美國「間諜法」控訴而成功引渡的案例。
這樣的影響會是國際性的,包括身為台灣人的我們,都應該意識到這樣的先例若是通過,將會影響我們每一個人跟「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也因為這層關係,我認為引渡阿桑奇是所有「非美國公民」都理應反對的,當然也包括我。在這種充滿爭議,且影響甚遠的案件上,英國不應該為了自己跟美國的外交關係,支持有「違反人權疑慮」的引渡程序。
起訴
第二個議題則是更關乎美國自己,但也是一個更根本的議題:阿桑奇的行爲到底是否違法?
如過不違法,那麼也不用談什麼引不引渡,因為阿桑奇根本就不該被起訴。這是許多美國國內媒體專注的方向,也是更多人討論的點,畢竟一石二鳥,只要美國政府撤告,一切就結束了。
在過去的判例中,最終大法官都站在人民這一邊,如上所述,媒體基本上還是擁有這一張免死金牌,但這張免死金牌存在有其理由。這部分,我最喜歡下面這篇社論的見解。下面擷取結論加上翻譯的段落中,作者說了為什麼儘管他很討厭阿桑奇的意識形態,卻仍必需要用「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尺度來看待這件事情:
Cognizant of how its prosecution of Mr. Assange under the Espionage Act could be used to target journalists for their everyday activities, th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who announced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in 2019 insisted that Mr. Assange “is no journalist.” But the Constitution does not define who qualifies as a journalist, nor does it bestow any such power upon the U.S. government. As the Supreme Court justice Byron White wrote in a 1973 decision,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is the right of the lonely pamphleteer who uses carbon paper or a mimeograph just as much as of the large metropolitan publisher who utilizes the latest photocomposition methods.”
意識到根據間諜法起訴阿桑奇先生可能被用來針對記者的日常活動,2019年宣布對他提起指控的助理檢察長堅稱阿桑奇“不是記者”。但是,憲法並未定義誰符合記者的資格,也沒有賦予美國政府任何這樣的權力。正如最高法院大法官拜倫在1973年的一項判決中所寫的,“出版自由的權利同樣屬於孤獨的傳單者,無論他是使用碳紙還是油印機,還是利用最新的照相排版方法的大型都市出版商。”
I find Mr. Assange’s ideology loathsome and his methods reckless. But the First Amendment wasn’t written to protect only those whose ideas, and means of expressing them, we find agreeable. As such, the continued prosecution of Mr. Assange under the Espionage Act constitutes a dangerous escalation in the government’s attempt to hinder free expression. In 1973, two years after the Supreme Court defended this newspaper’s right to publish the Pentagon Papers, a pair of eminent legal scholars referred to the Espionage Act as a “loaded gun” pointed at the media. That this legal weapon is now being aimed at an individual as unsympathetic as Julian Assange makes it no less of a threat to freedom of the press.
我認為阿桑奇先生的意識形態令人厭惡,他的方法魯莽。但是,第一修正案的制定並非僅為保護那些我們認為其想法及表達方式可接受的人。因此,繼續根據間諜法起訴阿桑奇先生,構成了政府試圖阻礙自由表達的危險升級。 1973年,在最高法院捍衛了紐約時報發布五角大樓文件的權利兩年後,兩位著名的法律學者將間諜法稱為指向媒體的“上膛槍”。現在這把法律武器被對准了一個像阿桑奇這樣令人反感的個體,這並不減少它對新聞自由構成的威脅。
我覺得他很好的跳脫了對「阿桑奇」這個人,究竟是英雄還是壞蛋的這個個人層面,並引用之前五角大廈事件的判決佐證:在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面前,人人平等,憲法沒有賦予任何人「決定誰是記者」的權利。無論你是一介草民還是大報社,都享有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因此,儘管美國政府不斷強調「阿桑奇不是記者」,卻不改變此行為違憲的本質。
憲法是為了保障人民的權利而存在,在憲法面前,政府制定的法律若造成「要保護的法益」與「侵害人民權利」不符合比例原則,就應該被判違憲。阿桑奇的案件中,「間諜法」不只侵犯了阿桑奇一個人的權利,更是相對給予了政府「決定誰受言論自由保障」的權力,這是對所有人民基本言論自由權益的侵害。
我認同這樣的論點,也覺得在我理解的美國法律框架下,撤訴是最正確的一條路。
我眼中的阿桑奇
說了這麼多「法律」、「法理」,其實都是最近看大家對於「這個案件的影響」整理出來的資訊而已。是時候回到這篇文章的主題了:我眼中的阿桑奇,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英雄還是罪犯
老實說,在剛開始接觸這些新聞的時候,最容易被一些阿桑奇的「義行」給感化,而順理成章地把他當作一個英雄。他做過非常多「正義」的事:創辦維基解密,專門披露政府醜聞等「人民應該知道」的事。也正因維基解密的爆料,國際上不少貪污政府遭到革命下台,完全就是一個民主正義的推手。在遭到美國政府迫害之後,仍然不願意屈服,而是以幾人之力對抗一整個國家。這是大家都喜歡的英雄劇劇情。
但上面這位紐約時報老哥的一段話(「我認為阿桑奇先生的意識形態令人厭惡」),也讓我覺得有必要用別的角度來審視這樣「英雄主義」的意識形態。阿桑奇以媒體人自居,認為自己有權力判斷什麼是「道德的」,什麼是「不道德的」,這何嘗也不是一種自負呢?
媒體道德的底線
在 2010 年的電報門事件中,維基解密最後解密的資料包含了大量「未刪減」(unredacted)的內容,及暴露了不少當事人的真實姓名,以及沒有必要的細節。儘管美國政府沒辦法證明這樣的行為對任何人造成了實質性傷害(因此沒有用相關罪名起訴他),但這成為當時許多媒體抨擊阿桑奇的一大原因:如果阿桑奇只是為了達到揭露證據,就算把所有資料的人名都打馬賽克,也可以做到一樣的效果,但他沒選擇這麼做,他選擇了開最猛烈的地圖炮,不怕犧牲一些「他認為罪有應得的人」,打出傷害最高的一擊。
很多人的反應可能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些人都活該!自己做壞事就不要怕有天有人會揭發出來!但我認為,這不應該是阿桑奇的角色,也不該變成他掌握在手上的權力。若他透過維基解密做的不只是「揭發」,而更是判斷誰該被清算、誰不該被清算,他就儼然已經把自己視為一個審判者,一切的標準由他心裡的一把尺所決定。這已經遠不止一個「揭秘者」的角色。
電報門事件的媒體夥伴們,也曾就此事聯合抨擊阿桑奇,他們認為發佈未經刪剪的資訊,無故讓吹哨者陷於危險,聲明中稱「我們無法為公開為刪減資訊的行為做辯護,這一切都是阿桑奇一人所為」。

顯然,在一些「媒體人」眼中,阿桑奇已經跨過了作為媒體的道德底線:他把自己當作一個審判者,而不只是簡單的媒體人。
在支持阿桑奇的那一派中,偶爾會看到具煽動性的言論,例:「美國的媒體都被美國政府控制了!在電報門之後全部都轉為支持美國政府那一派,倒戈維基解密。」這樣的說法是不對的,這些媒體確實有脈絡可循的對維基解密從支持轉變為反對,知道上面這段故事,也知道為什麼上面那位老哥會說他手段魯莽了吧。
但踩線歸踩線,儘管媒體界大家好像不喜歡阿桑奇,不代表這個起訴事件上沒有站在他這邊。上述的五家電報門媒體夥伴,就曾聯合為了阿桑奇發聲,寫了一封公開信 :An Open Letter from Editors and Publishers: Publishing is Not a Crime。信中他們再次重申:「當年對於阿桑奇公開未經刪剪的電報文件,有必要公開批評他的行為 … 但今天我們也是為了這個案件聚在一起,表達嚴重關切。 … 這次起訴設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並威脅到削弱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和新聞自由。」
網路自由的捍衛者
上面說了不少有點反阿桑奇的話,大多是針對他身為「媒體人」這樣的人設,以媒體人來說,我覺得他或許真的太自大了。因此,我不會把他當成一個毫無缺點的聖人。
但或許因為這些維基解密的新聞、政治關係、以及這場司法對決的終極論是媒體最在意的「言論自由」,這一切讓我們無形間忽略了阿桑奇的本質:他這個人究竟是誰?除了媒體人以外,他還自詡怎麼樣的角色?
我認為,稱他為一個勇敢的「網路自由捍衛者」,豪不誇張。
在 Cypherpunk 這本書裡面,透過阿桑奇跟另外幾位網路圈大神對於「網路自由」的討論,可以有跡可循地看到更多他思想的來源。書中提到,他一生最大的兩個推廣脈絡是:
後半段這句,Transparency for the powerful,是大家廣為人知的維基解密在做的事情:用透明化的方式,減少掌權者與一般人民之間不對等的資訊落差。但較少人知道的是,他也同時是用一生在貫徹 “Privacy for the weak” 這樣的理念。
他不斷在各種場合推廣「加密」,因為這是讓網路得以維持「自由」的唯一手段。他在書中這樣說:「如果你曾經因為宇宙允許殘忍的核武存在感到難過,那也應該為宇宙中存在著加密而感到欣慰。」透過數學,宇宙給我們一個方法保護自己,確保我們有權使自己的通訊訊息無法被武力所破解,在任何地方都保有隱私。
這是我聽過對於「加密」這件事情最浪漫的解釋了。
Mass Surveillance
他也提醒所有人保有對於「網路監控」的意識:早在 2010 年出,Facebook 社群媒體各個起飛時,就無數次公開警告:網路已經成為每個國家政府都用來監控人民的手段,而人們正被網路的方便衝昏頭,自願地把越來越多本來該被當作「隱私」的東西,自發地交到網路上、以及大公司手中。
書中舉了個例子:網路的監控比古早時代的監控簡單多了,成本也低多了,幾百萬歐元就可以儲存整個德國一整年的所有通話紀錄(這還是十幾年前的數據)。因此現在的政府監察機關不再有動機「篩選」,在這樣低成本的網路世界,所有資料都先記錄下來就對了。相較於以前政府要監控一個人要先有搜索票等等,並且付出相對高昂的成本,現在的監控邏輯,則正轉向無差別的大量監控 — 即為 Mass Surveillance 。這是一個專有名詞,建議有興趣的點進去看更多細節。
可能有人會覺得,政府哪會這麼閒自己做這件事情。但要意識到:1. 政府不必自己做「蒐集」這件事,因為他們可以透過跟電信商或科技公司的合作來達到目的。維基解密的抓查事件中,華爾街日報就曾報導過許多公司反映美國政府在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脅迫各家公司提交關鍵個資。2. 在該事例中,依照某些國安法面前,美國政府甚至不需要向法庭揭露目的與相關證據。
阿桑奇身為最早一批的網路使用者,在十幾年前就開始推廣這樣「無差別監控」底下的人權。他很清楚新一代的「網路原住民們」正不知不覺中放棄的東西。我們每一個人現在在網路上每天受到的監控,可能比 30 年前任何一個殺人通緝犯還要多。
網路是否是戰場
從這個大監控角度出發,更讓我忍不住要把他重新封神的,是他對於這個世界的又一個精準觀測,也是一個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討論的問題。他說:「所有的人都在討論 “Cyber war”,但沒有人討論 “Cyber peace-building“。」他認為,這是因為「戰爭」是美國政府學習到網路這個技能後,本能想要套用的第一反應,並且不斷地把這樣的意識形態灌輸給世人。
Jacob Appelbaum (另一位美國的網路大神) 在書中提到:網路在快速「被軍事化」的同時,這樣的意識形態也在不斷輸出:各國訓練的「資安人才」,其實就好像訓練士兵一樣,試著訓練出能夠快速「攻擊」敵人破綻、或是能夠有效「防禦」攻擊的人。如果我們跳脫出來,會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為什麼網路世界的破壞,要被比喻成戰爭中的攻擊,而每個人保護自己系統、自己隱私的行為,要被比喻成「防禦」。他說,那場他受邀參加的資安研討會,最後讓他感覺像一群整天想著打仗的美國軍人,在莫名其妙的把他們的價值觀強加到所有人身上。他覺得「網路」與「資安」不只是如此,但是卻被描繪成一個戰場。
這讓我想到:前面所提到的,這個「新時代隨時隨地都是資訊戰」的想法,也正是一些政府主張並大力宣傳的論點。這或許也讓為什麼「我們每個人都該被監控」、「我們可能會被當作間諜」更具有說服力。畢竟國家在打仗,這是為了守護整體更大的利益。但這真的是真實的嗎?
P.S. 這裡說的資訊戰,代表偏向傳統資安、駭客間的攻防,不適用於新時代的「策反、散佈假消息」等等範疇。
資訊戰肯定是真的,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說資訊戰不真實就真的太荒謬了。但這裡值得深思的另一個問題是:這個「戰爭」狀態的比喻,適用於我們跟政府之間嗎?
人民與國家是戰時關係嗎
仔細想想。我們與國家之間利益,其實許多時候是相違背的。不要忘了,政府也有自己的目的(Self Interest),因此常常希望獲得人民不想要給出去的資訊。無論他們要做什麼事,獲得大家的資訊對於掌權者幾乎總是有利的。從這個角度想,國家有在教我們如何保帳自己的「資安」或「隱私」嗎?我認為沒有,反而我們的資安做的越好,政府越不容易管我們。
所以美國政府口中的「資訊戰」,並不是要每個公民保護好自己,而是相反地正在塑造一種:「這個東西可怕又困難,這個東西人民自己學不會,外國駭客整天都想攻打我們,就讓國家來保護我們吧」的戰爭情懷。而國家「保護」人民的方法,是實施更全面的網路控制。
許多政府的不願意讓我們「人民」對他們的監控有所防範,他們往往可以靠「打擊犯罪」的這張金牌,強制人民放棄隱私權(Tornado Cash 就是最好的例子)。遇到像維基解密這樣不願意向政府低頭的存在,就把它稱為「恐怖份子」(美國政府多次稱呼維基解密為資訊恐怖份子)因為要保護大家,因此任何政府不能掌握,不服從的行為,就是叛國,甚至被歸為恐怖主義。
想到這裡,回頭看看阿桑奇因為「間諜法」這種戰時法被起訴,只覺得格外的諷刺。阿桑奇早就預言了各國政府正將大家對於網路的隱私與自由,透過「戰爭化」與「國家化」的意識形態加以剝奪,不知道他當時有沒有想過這一切不但應驗,還硬生生的強加回他自己的身上。
或許西方國家一邊嘲笑中國的「天網」荒謬侵害人權,一邊正舉雙手歡迎自己的國家正以正義為名,做著一模一樣的事情:一場全面的網路監控已經悄然降臨。

Julian Assange, a Cypherpunk
雖然書還沒看完,但我認為我已經對網路是什麼,有了不少新的想法。也更理解阿桑奇除了目標「為強者施以透明」外,要傳達的另一重要資訊:我們每個人身為相對弱勢,該怎麼樣保護自己?
在我們這群網路新住民心中,很多東西已經是理所當然,我們也忘了要去置疑。現在基本大家都慢慢接受,自己的住址電話等個資早就已經毫無隱私可言,甚至我們去了哪裡、跟誰通過話,這些早就都不屬於隱私的範疇了。但稍微理解者個十幾年尺度的網路革新後,也讓我不禁感嘅:這個變化來的之快,什麼是「隱私」,什麼值得自己保護,我們這一代人是不是放棄的太快了?
看了阿桑奇的人生經歷後,能夠多少體會他一路看著網路從一個單純、人人平等的遊樂園,淪為一個戰場的感慨:網路正變的比真實世界更加集權。
我想,在他的心目中,一定希望網路是如同一開始一樣,是一個自由的地方,它不必與戰爭或是國家攻防相綁定,也不必淪為極少人控制人民的手段。但人們需要有意識地,去了解這個新世界的運作方式,並不再以「享受服務」為理由,犧牲自己應該保有的基本權益。
Julian Assange,他是個浪漫的自由主義者,也是個為了自己的信仰,勇敢站出來捍衛價值的人。他或許不是一個完好的媒體人,但他正用盡他所有的力量,推廣網路自由、網路隱私的基本權益,他正努力捍衛大家免於一場只有極少數人預見的災難。
我一直很喜歡這種 cypherpunk 的精神。我想,阿桑奇在我心目中,就是最典型的 Cypherpunk。
我想,這或許是我對他能給出最精準,也是最高的評價了。